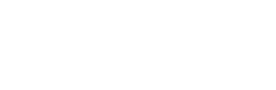孙泰雁
(上接11月3日三版)
市场经济在提升人们独立人格意识的同时,也诱发了一些个人本位主义的不良现象。一些人过分强调人生的自我设计、自我奋斗和自我实现,把自己与他人、社会对立起来,只讲个人利益,不讲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只顾个人需要,不顾他人需要;只要个人自由,不要组织纪律。据对武汉地区高校640名大学生和600名研究生的调查显示,“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选择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占81.4%。
个人本位主义包括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其共同的本质特点是:把个人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强调个人利益高于一切,把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看做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一切言行都以个人利益得失为转移。极端利己主义甚至不惜损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唯利是图、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就是对个人本位主义的诠释。个人本位主义是私有制的产物,自从私有制出现以后,个人本位主义的思想和倾向就存在着,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本位主义成为一种社会病。
由此可见,个人本位主义侵蚀着社会伦理道德,破坏社会正常秩序,导致社会责任感淡化。责任,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工作和所属群体、共同生活的社会所承担的任务及其应尽的义务的自觉态度。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它就是社会对生活于其中的成员的一种规定、一种使命,是一种无可推脱、必须完成的“任务”。
责任既是一种道德认识、道德态度,更是一种道德行为的实践。当一个人能够积极地行使他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时,社会才能有序地运行。然而,在我国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伴随着个人本位主义的滋长,出现了许多无责任现象。在经济关系中,一些人为了谋求一己私利,大肆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制造传播文化垃圾,进行各种欺诈活动,造成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坑害国家、坑害集体、坑害他人。在人际关系中,一些人心态冷漠,见义不为,见难不帮,见死不救。令人担心、寒心和痛心。与此同时,激发对物质利益大胆追求时,少数人在一定程度上滑入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泥坑。利益原则既是经济主体的原动力,也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正是在各个经济主体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促使了技术的改进,推动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是多劳多得。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的目的,就是要借助利益激励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力地冲击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鄙视物质利益的“精神万能论”,人们不再忌言利,恐言富,而是积极大胆地去创造,去追求劳动所得。中国社科院为考察转型时期人们对待“工作与挣钱”的一般态度,对“干活就是为了挣钱”这一社会上颇为流行的说法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很赞成”或“基本赞成”“干活就是为了挣钱”这一说法的分别占18.61%和48.97%,合计为67.58%。这就意味着,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利益意识觉醒后,并未走向积极健康的思想境界,而是陷入了不健康思想的漩涡之中,他们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将“精神万能”变成“物质万能”,总是有意无意地贬低精神的价值,甚至使“精神”变成“物质”的奴隶。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滋生蔓延。
拜金主义是一种对金钱顶礼膜拜的思想观念。拜金主义者过分强调金钱的力量,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们的行为、社会生活和人的价值,都以金钱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冷冰冰的金钱关系。金钱本身仅是价值的尺度、交换的媒介和聚财的手段,并不包含善恶的价值判断。由于人们对金钱的本质的不理解,产生了一种盲目的推崇和依附心理,从而产生金钱拜物教。在拜金主义者眼里,金钱是万能的,金钱使人迷醉,使人疯狂,使人激动。于是,一些人为了金钱,可以蔑视理性,捞钱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甚至干出丧尽天良的勾当;一些人为了金钱,可以无视法律,铤而走险,把党纪国法统统抛在脑后,践踏一切人类文明;一些人为了金钱,可以抛弃道德,什么良心、荣辱、责任、义务以及生活准则,全部踏在脚下。现实生活中的走私、造假、贩人、贩毒、卖淫、贪污、杀人越货等,都是拜金主义的具体表现。中国社科院“转型时期伦理道德建设的难点与对策”课题组关于“钱在生活中的地位”的调查显示,有11.3%的人认为“钱是人的能力与价值的尺度”。对“要赚钱就别讲良心”的说法,调查显示,有37.66%的人认为“有些道理”,另有9.99%的人甚至认为“确实如此”。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享乐主义是一种把寻求肉体感官享受当作人的本性,视人生目的就是为了追求个人享乐的思想观念。享乐主义是近代资产阶级打出的人文主义旗帜,在反对封建的禁欲主义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在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享乐主义时,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纵欲主义的泛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但也出现了享乐主义的现象。一些人迷恋于对物质的享受,往往超常消费,一掷千金,追求“帝王”享受;一些人追求庸俗文化的享乐,嗜黄碟、黄书,在黄色下流的碟片、书刊中求快乐;一些人追求自我麻醉的享乐,赌博、吸毒,将生命淹没在聚赌豪赌中,在吸毒的吞云吐雾中求得人生快慰;等等。享乐主义是物欲横流的一种表现,若不加以限制,任其自流,将导致人的理智丧失、自甘堕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调查发现,一些人强烈渴求科学文化知识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政治观念淡化的不良倾向。市场经济的运行充满着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竞争的实力,来自于科技的领先和超群。国际间的竞争,是以科技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国内市场主体的竞争,同样是以科技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实力的较量。只有拥有第一流的科学技术和第一流的科技人才,才能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市场经济竞争的客观要求和科学技术竞争力的凸现,唤起了人们对科技文化知识的高度重视,激发了人们学习掌握科技文化知识的兴趣。
当前,在我国各大中城市里,各种科技文化知识的培训班层出不穷,报名学习者络绎不绝;各类高等院校招收的大学生、研究生数量不断扩大,升学热、考研热持续升温;先行致富的“大款”阶层中,重返校园攻读学士、硕士学位的不乏其人;有知识、懂技术的专家学者中,被企业高薪聘请者比比皆是。在农村,“要致富、学科技”的思想已被愈来愈多的农民所认识、所接受,学科技、谈科技、用科技蔚然成风。科学种植、科学饲养、科技兴农、科技致富已成为一种潮流。
在人们注重学习科技文化知识的同时,一些人又存在着政治观念淡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一是信念缺失。一些人认为,现在搞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了,过时了,因而出现了不理会甚至回避、厌烦、鄙薄马克思主义的情绪。二是理想错位。一些人认为,“理想是远的,道理是虚的,唯有金钱和享乐是真的”,似乎除了金钱和享乐之外再没有什么值得追求了,国家的前途、人类的理想往往抛在了一边。更有一些人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捞票子,讲政治值不了几个钱,因而对讲政治不感兴趣,不屑一顾,甚至冷淡、反感。在这种氛围下,党和政府所倡导的远大共产主义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往往被视为不合时宜而遭到他们的讥讽;所弘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常常被看做是政治说教而受到他们的贬斥。
要知道,社会风气的二重性,展示了攻坚时期社会风气的总体状况。在这二重性中,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是主流,是基本的东西,我国整体精神面貌是在走向进步。独立人格意识的形成、利益意识的觉醒、对科技文化知识的渴求,不仅是对传统思想观念的巨大冲击,更是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大多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当然也是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如果让其自流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总之,把握主流才能做到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重视问题才能做到不“一俊遮百丑”。
良好的社会风气需要一系列健全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作保证。离开了这一保证,便会诱发不良社会风气的滋长、蔓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安排,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思想得以生成、发展的基础。但在现实生活中,为这一基本制度所要求的一系列具体制度,却远远没有达到健全、完善的境地,许多方面仍处于艰难的探索过程。由此,不可避免地在经济生活中将存在大量的制度管理不到位、不完善的空间。正是有这么一个空间,才使得生产领域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交换、分配领域的偷税漏税、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损公肥私,以及消费领域的享乐主义、物欲横流等各种丑恶现象大肆滋长、蔓延。这些现象诱发出一种与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和道德观念格格不入的生活哲学:如“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捞一把是一把,不捞白不捞”、“今朝有酒今朝醉,不醉白不醉”等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价值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但如何将这一价值原则具体落实到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即政治体制之中,也仍然是一个探索中的课题。长期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着政企不分、权力过于集中、官僚主义、家长制、以权代法等弊端,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克服了以往政治体制中的某些不足,但一些问题的惯性仍然存在。实际生活中,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家长制、一言堂等现象还经常发生;那种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刑不上大夫的情况也时有出现。尤其是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党内产生了较严重的腐败现象,并有日益蔓延的趋势。腐败是对党的宗旨的背叛,是对人民利益的侵害,也是对人民的权利和主人翁地位的挑战。它不仅败坏了党风,损害了党的形象,导致党的威信下降,也使一些人对党产生不满,出现信仰危机和政治淡化现象。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还很不完备,还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再加上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的不良影响,人们的法制观念还比较淡薄。因体制转轨而引发的传统法制的瓦解与现代法制的生成难以同步,由此造成法制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某些领域出现了“真空状态”,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助长甚至进一步恶化了不良的社会风气。
(未完待续)